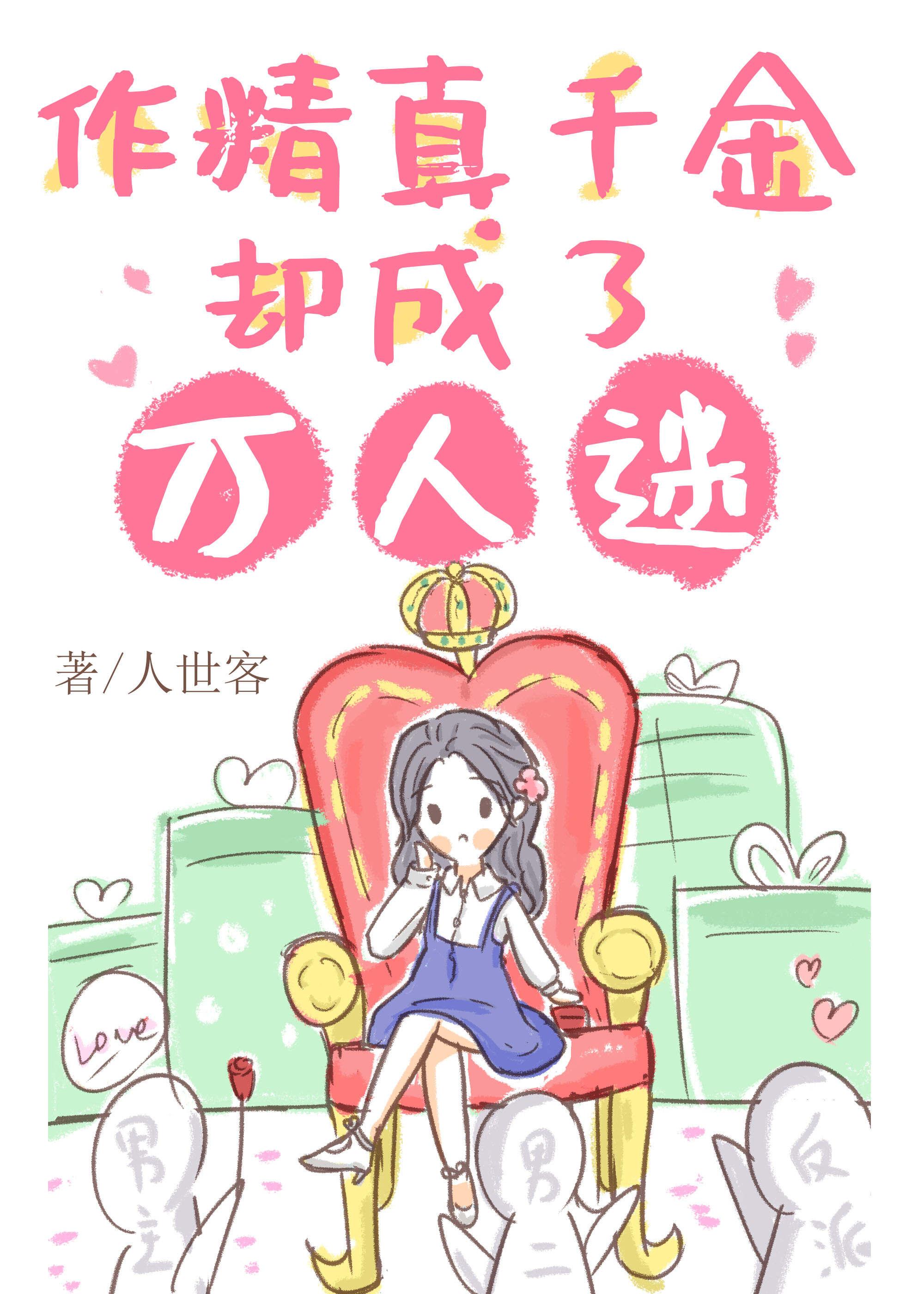落秋中文>半世私情 > 第三章04(第8页)
第三章04(第8页)
格里斯始终开张着嘴,药片停留在舌根部位。她就取来了水,朝它的口腔灌下去。格里斯顺从地嗫嚅了口舌,药滑了进去,它的眼里流露出大惑不解的情色,陈惠蓉幽暗的心中动闪了些许光亮……
奇迹最终没能出现。
过了,一日。
夕阳烧红了半边天。格里斯在沙丘上晒了一天太阳之后,一步三晃朝陈惠蓉身边来了。它已瘦得皮包骨头,光光亮亮的皮毛已如冬叶秋草般枯涩。刚刚将羊只领回圈的陈惠蓉被不祥的预感紧摄着,倚墙而立,惶然地瞅望着它。格里斯似一位耄耋老人,生命之火奄奄欲熄,每走一步都像有立即倒下的危险,松松垮垮的腹像一只空空的口袋,一摇三摆,目光却是平静安详的。
陈惠蓉迎它走了几步,到它跟前,俯下身,用发抖的手轻轻抚摸它的一身乱乱蓬蓬的黄毛,从头顶脖颈至那条已失去分量的尾巴。格里斯默默地享受着最后的温存,一双红眼睛流露着惬意和感动。
它是积聚起最后的力气,来向她告别的。
太阳沉落到地平线上,旷野笼罩着凄怆的暮霭,大地在静寂中发放着惨壮的悲歌,料峭荒风冷透了人的心。
格里斯倒下了,它倒在粗沙沙的黄土地上,一双善良淳厚的红眼睛紧紧地闭合了,永远不会再睁开,它不舍这空旷荒原中的缕缕温暖之情,不舍离开孤独之水浸透了心堤的女主人,可它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这样不合时宜地向草原作别,向她,永远地作别了!
陈惠蓉痛哭失声,为逝者,为自己。满腹的恋情和忧愁在倾泻如潮的泪水中汹涌。
她请一名会木工的战友选择上好的木料,为格里斯精心制作了一口小棺材,将它瘦嶙嶙的尸体安放在其中,在“孤岛”正南方向的一座高高沙丘的向阳处掘开深深的墓穴,睡着格里斯的木棺放进去了,她最后一次揭开厚重的棺盖,可爱的格里斯似乎觉到了身后这非凡的待遇,面目情色十分地舒畅。缓缓的风自东方吹来,一束新鲜的阳光洒入洞穴,打在它无觉的身上,陈惠蓉默默地久久地守坐在格里斯的身边,心被重锤一下下敲击着,眼里滴出浸血的泪花。格里斯死了,它是满怀忠诚和友爱离开这光怪陆离的世间的,它在患了疯症,病入膏肓,完全混乱了意识的情状下竟然未伤一人一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它凭着超常的友善之心切实地做到了,多好的格里斯呀!
默默地久久地在它的身边坐着,用心向它诉说着别情离绪,当草叶上的露珠痕迹净无的时候,她恋恋地俯下身去,将红红的棺盖闭拢,一锨一锨洒下黄土,将洞穴封得严严实实,不让阴冷的冬风和炙热的日头侵扰它的安宁。面前这座庄严的坟丘,她会永远记着的。
四面八方弥**着沉死的气息,陈惠蓉不知道怎样打发有野狼出没的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整个“孤岛”犹如一座大坟场,她摇着疲惫的身躯,一步步在里面走着。
陈惠蓉在忧愁和沮丧的情绪中打发着没有前景的日子。常常感到恐惧。
恐惧至极,便激励出一拼一搏的勇气。
整理了简单的行包,奔往家乡古城,做破釜沉舟的一战。
古城的景气依然是死沉沉的,初夏灿烂的阳光没使它些许明快。
家门的铁锁该是锈迹斑斑了吧,手中的钥匙却是明光闪闪的。
习习晚风吹着,她临近了熟悉的小巷,转进杂陈的院落,旧居屋中有灯亮着。
开门的是陌生的面孔。她说:“你是谁?”
“你找谁?”陌生的脸孔反问。
她被拒在了门外。房屋已易了主人。
“怎么会呢?房证在我的手里呢!”她辩讲。
“房是公家分我的。”陌生人道。
“可是我们也得有处住呀!”
新主人也表示了对她的同情,可自己也有自己的难处。
屋中原有的东西也不知被公家搬到哪去了。
她无言可辩。心中满积着愤懑,走开了。
小巷的悬灯如同一只被打充了血的眼珠子,发射着晦暗的幽光,长长短短地抻拉着她踽踽的影子。她迷茫地自小巷走出,滞立在十字街头,忧忧地想,此身该往何处去呢?
此时的陈惠蓉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那进退维谷的境地。不错,五年光阴,城街依旧,屋宇依然,但心情却并不十分相同,经过边塞凄风苦雨的抽杀击打,她自信是具有了应付这千奇百怪之世界的能力,人成熟了,心坚强了,人生就是在茫茫大海上飘泊的小船,前也是浪,后也是浪,左也是浪,右也是浪,怎么也是在浪心儿上飘**,就无所谓祸与福苦与甜了。
今夜栖身何处呢?
想到五年前在省城客宿洗澡店的经历。此时也真该痛痛快快洗个澡,同时下榻,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几家面向社会的洗澡店。走了好远,找了两处,都已紧闭了门板。此城没有又洗又睡的堂所;她有点犯难。
舍不得花三四块钱住店。不止过这一夜,或许要呆上十天半月,住得起么?
就走到了火车站的候车室里。
几大排长长的木椅,没有多少人占用。躺上一睡,也挺惬意。
现在不比去边疆之前,不怕持阶级斗争观念的巡逻人员前来盘查。自己有了一块很铁的牌子——中共党员。红彤彤的党证揣在怀中,共产党员,能是阶级敌人么?边疆五年苦战,并没有白费,自己这样的出身,进到了党的组织,确是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