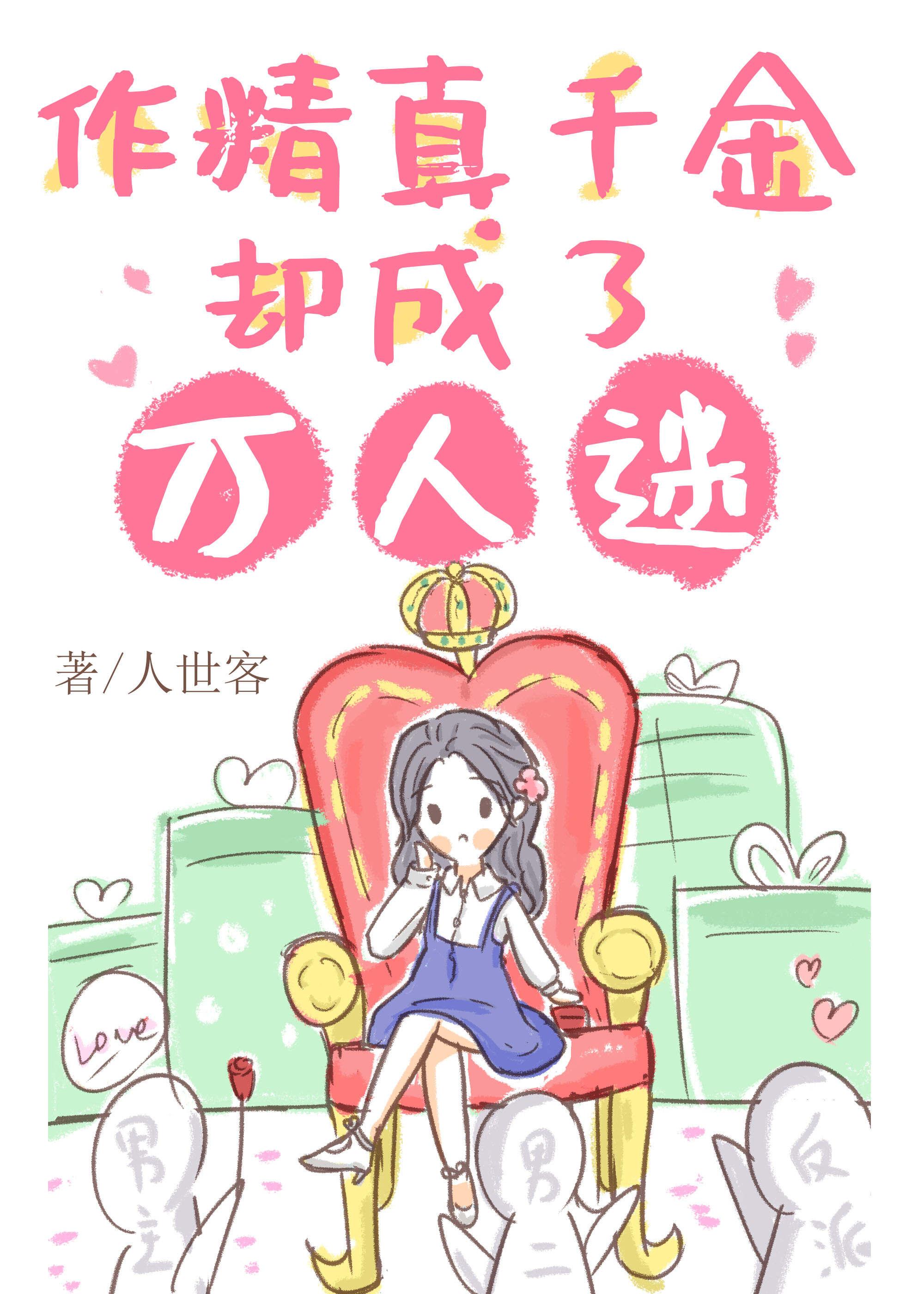落秋中文>半世私情 > 第三章04(第7页)
第三章04(第7页)
“唉……”
“叹什么气?”
“你们男人全都是无情无义。”
“别瞎扯了。”
“当然。”
“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也不问一问。”
男人不再言声。老话题了。过去的事已不可挽回。
两条身子紧紧地拥着。她一刻也不想放松。这本该属于自己的人儿,阴错阳差,让命运安排到别人那里去了。怨谁?似乎谁都该怨,又谁也怨不得!
那年……
那年,肖梁走了,把塞北大地新鲜空气带走了一半。
她只能把沉重的心事掖藏起来,一股劲地奔前程。只要有了好的前程,才能缩短和他的差距,才有希望把他揽回在身边。团人了,下一步得尽快加入党组织。
章指导员对她是客客气气的。客气得有些谦卑,有些诚惶诚恐,有些敬而远之。陈惠蓉不愿意看到她那副样子,她不愿意充当伤人之箭骇人之虎的角色。
她的入党问题,在章指导员的积极运筹下,不久就获得成功,这在全团大概也算是特殊事例。凭她那稀脏的出身,进到这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来谈何容易,她办到了。指导员其中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可想而知的。账应该是彻底清了,谁也不欠谁了!但章永红还是像欠她什么似的,仍然努力地帮她,她当上了班长,没多少日子又被提拔为副排,继而是排长。
陈惠当然欲望着继续高升,但连干部职位近期不会有空缺。章永红有一天突然来告诉她说,自己要调走了,调到乌海渔场去。陈惠蓉心里就有些不大自在,真诚地说:“你不要去吧,我们在一起多好,我一定加倍支持你的工作。”章永红眼里就闪出点点泪光,说:“已经联系好了,那边的条件也好些。”
然而,过了好长时间,指导员也没能走掉。说是联系好了的,那边变了卦,又不收了。
这时,兵团即要解散的保着密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出,一些军人们已经开始了撤离的准备。表现是对本职工作敷衍了事,有人又打箱又造柜,用公家的木材和人力也不讲什么学习张思德了。人心便惶惶然起来。不久,就有准确明白的情况报告出来,军人干部要全部撤回部队,这里的知青交地方管理,兵团变成农场。同甘苦共患难的领导们的振翅高飞,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知青们的感情,大家也都紧张地行动起来,各自寻找回归城市的门道。以往零敲碎打地返城情况变成群体的声势浩大的形势,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豪言壮语豪情壮志成了一张旋飞在冷风中不知落处的废纸,塞北的雪雨似乎更加冷酷更加无情了。
困、病之说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瞒哄事,但于陈惠蓉来说却依然是关山重重。精哄也得出点力气,可陈惠蓉故乡城里已无亲无故,困退就没有了口实。病退,自己虽在这边的医院里取了证明,也寄给了家乡“知青办”,却因城中无人奔波活动,办成也无甚希望。心中火烧火燎地急。
同一战壕中摸爬滚打的战友们,一个个办了告别的酒会。每一次替别人高兴之后,她的心头都加添一番沉重几分凄凉。痴痴地站在黑黑漆漆阗寂无声的原野,仰望满天无言的星斗,听八方刮来的不知人间悲与愁的边风,可怕的孤独感就箝紧了她的心,浑身会不由自主簌簌抖颤。
指导员章永红在大撤退的洪流汹汹涌涌的时候始终不动声色。她曾经在无数场合喊出过扎根边疆干一子革命的钢铁誓言,也曾经将不安心边疆工作的人斥责为懦夫逃兵而嗤之以鼻。她当初虽也有离走的意思,但那只是这边陲之地的调动,并不是去贪图城里安逸的日子。在兵撤如山倒的今朝,她冷眼相观,不再以学毛著积极分子、党的政治工作基层领导者的姿态施令演说,也不随波逐流“蠢蠢欲动”。
当昔日繁华喧闹的土地变成冷冷清清的“孤岛”的时候,陈惠蓉与章永红的关系似乎变得亲近起来。为离开这片土地,女知青们将青春肉体依许给权力人物的事情屡见不鲜,指导员的耻辱已淹没在了汪洋大海之中不足为奇了。这“孤岛”上最后所剩的两人兴许就是自己和指导员了呢。陈惠蓉这样想,同时就生出同病相怜的感情。
此时的陈惠蓉格外地思念起了肖梁,日日重温着与他相处的良辰差时。想给他写封信,笔提起放下,不敢冒昧,她幻想着突然一天能接到他的来信,水冷冷的希望最终浸没在一片荒沙之中了。
“孤岛”上的人员还在不断地减少。八十,五十,三十,任何人已不再做什么建设边疆的活计,此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奋飞者将要编入当地农业组织,此时,这组织还是空散着的。强大的潮流面前,最能沉得住气的也难免心神摇动。
依同所有的知青离别的程序,章永红的走也少不了一场送行的浊酒。阴风惨惨之夜,陈惠蓉喝了个酩酊大醉,想到与指导员那刀钩剑戟的交战,想到自己日后零仃无依的苦景,百感交集,两人相拥,嚎啕痛哭了一场。
凄凉的“孤岛”上又有了狼的嗥叫声了。陈惠蓉把肖粱喂养大的格里斯收留在自己的身边。为壮胆,更为排遣忧愁寂寞。格里斯长得又高又大,威武雄壮,那条金黄中划着一条雪白的毛茸茸的大尾巴摇动起来分外婀娜。它老成持重,步履坚定,一副忠贞不渝的喜人神态,为陈惠蓉刻板的生活加添了一丝春风暖意。
一九七六年的春季在一片懒僵僵的气氛中跚蹒而去。广大知青抛洒了滂沱热汗开垦的千亩良田已然荒芜长出萋萋青草,远方村庄的牛羊们间或悠悠而来,把狼的嗅觉也牵引到了这里。
狼是怕狗怕人的,它们叼羊咬牛本也是为着自身的生存,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境下绝不冒枪弹和刀斧的危险。为了防范狼的袭扰,人们除了用武器相对,还设置陷阱和钢铗。上过当的狼们总结传授过惨痛的经验,更不敢贸然行事。然而,在一个明光朗朗之日,有一只大狼竟然不紧不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孤岛”上,它的目中无人的神态使岛上残存的居民大为惊诧。狼的无所顾忌的行为激怒了刚从草甸上戏耍归来的格里斯,它箭一般向大狼射去。狼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仓惶逃窜。格里斯奋勇追击,跑出十几里地,大狼突然停住了脚步,掉转过身来,亮出尖牙利齿与扑冲上来的格里斯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陈惠蓉和另几名知青持铁锨木棍朝认定的方向追出来好远,却不见格里斯的踪影,又转变方向一番寻找,仍无所获。大家为之焦虑。
太阳西斜的时候,格里斯返回了“孤岛”,它的步履疲塌无力,陈惠蓉惊喜地迎它上来,只见它那低垂的头脸上满是血污,身上的毛鬃被汗水血水粘拧得条条圪圪。
陈惠蓉俯下身,心疼地将它搂在怀中。格里斯软软地倒了下来,慢慢地阖上了眼睛。
格里斯此次远程出击,正犯了兵家大忌。一般情况遇到狼的偷袭,只需一阵狂吠将它们吓跑了事,真正的厮拼格斗是人们的事,狗的能力只可配合,因为狗们一般是敌不住狼的铁嘴钢牙的。这点格里斯不是不懂。这次它的孤军深入,一是迫急地想一展雄风,再就是此狼在光天化日之下独往独来的狂傲之态令它怒火中烧,头脑就热得失了控制。
听了这番预断,陈惠蓉的神经万分地紧张起来。勇敢忠诚的格里斯是她这颗孤独伤感之心的唯一安慰者。有它的影子在身边,就好像有肖梁的气息游绕,它是肖梁一手抚养大的心肝宝贝,是他带不走的精灵。她默默地为格里斯祈祷,一向不信上苍不信鬼神的她,面对一轮满月,向神明求助了。
然而,命运之神并不理会她的虔敬之心。格里斯的气态明显地不对劲儿了。原本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已变得无精打采,矫健的步履已木滞迟钝,头颅萎靡地耷拉着,整天也不见抬起,吠叫之声也乏了昔日的豪壮,再好的东西也吃不起精神,懒懒洋洋慵慵惫惫,全然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陈惠蓉不寒而栗了。为了使格里斯重新健康起来,她带着它奔出几十里地到公社兽医站求办法,兽医问了情况,检查了格里斯的身体,认为确是中了疯毒,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陈惠蓉从兽医那里取了不少的大白药片,回来后一片片喂给格里斯吃。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失去了理性的格里斯是绝不会欢迎苦药片的,而让它下咽的办法只能放在它的口中,因为它已经不食不喝,掺在食物中已无法喂进,万一格里斯性情发作合嘴关牙,受到损伤的人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但她不能作那么细密的思考了,救格里斯的命,微茫的希望就在这解毒药上了。她轻唤着它的名字,弯下腰,托起它的下巴,把四只药片塞进了它的嘴中,它不**也不闭嘴,药片稳稳地贴在红红的舌头上。
“格里斯,把药咽下去,咽下去你的病就好了。”她亲柔地对它讲着,格里斯呆痴着无动于衷。陈惠蓉就伸出了食指,把白药片向它的嗓口推了推,手指贴上那湿热的舌,触着了深处的牙床。她的腿微微抖颤,汗水刷刷地淌下来。